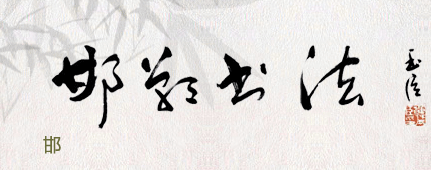详细内容
谢权熠读有关褚遂良资料札记
谢权熠:读有关褚遂良资料札记
壬午年秋习唐楷课一月,其中习褚遂良《阴符经》三周。此前笔者对褚法帖注意不多,三周下来才发现褚书的高深。癸未年二月又有楷书课数周,笔者又遍临褚书,受益良多。《书断》云:“(褚遂良)真书甚得其(虞世南)媚趣,若瑶台青琐,窗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此决非过誉之论。
3月6日笔者翻手头书籍有关褚遂良条,大概了解褚遂良生平、书风及影响。现先抄录《旧唐书第十八卷·列传第三十卷》中记录,以对褚遂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介绍:
“褚遂良,散骑常侍亮之子也。大业末,随父在陇右,薛举僭号,署为通事舍人。举败归国,授秦州都府铠曹参军。贞观十年,自秘书郎迁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太宗常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太宗常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齐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
“十五年……其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
“十八年,拜黄门侍郎,参综朝政。”
“二十年……其年,加银光禄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检校大理卿,寻丁父忧解。明年,起复旧职,俄拜中书令。”
“永徽元年,进封郡公。寻坐事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征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其月,又兼太子宾客。”
“六年,高宗将废皇后王氏……左迁遂良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转桂州都督。未几,又贬为爱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
“神龙元年,则天遗制复遂良及韩瑗爵位。”
《旧唐书》对褚遂良开篇既以书法家身份出场,可见褚遂良影响首在书法一艺,褚遂良“甚得王逸少体”即召为侍书,其中也有上好“二王”的原因。其晚年楷书多见“二王”行法,用笔也在欧虞基础上加之以轻细和滋润,宽绰疏逸、丰润劲炼,启立自家门户。这种变古制令使褚书“丰艳雕刻,或为当今所尚”(李嗣真《书品》),使魏晋流风一变而尽,开唐代楷书门户,影响以后徐浩、颜真卿诸家。毛枝凤《石刻书法源流考》云:“自褚书即兴,有唐楷书,不能出其范围。显庆至开元各碑志,习褚书者十有八九,诸拓俱在,可复案其时代意义非“唐之广大教化主”(刘熙载《书概》)不可当。
二
上文介绍褚遂良生平时,基本用了《旧唐书》的资料。其中载褚遂良卒于显庆三年,六十有三。笔者读《书断》时发现身为唐人并出任翰林院供奉的张怀 却说是“显庆四年卒,年六十四。”查《旧唐书》之成书,在于后晋天福十年,经后梁、后唐等收集野史、日历、除日、朝报及实录而成。《旧唐书》修纂时离唐灭亡只有40年,不少编修者都是唐末出生的,由他们来修唐史有“时近迹真,见闻亲切”的有利条件。另外,唐代官方本身就很重视整理自己的历史,从唐初以来,经令狐德 、吴兢、韦述、柳芳、于休烈、崔龟从等人不断修纂大体上中唐元和以前已有了纪传和编年两套粗具规模的国史、实录。后梁、后唐不断收集史料,许多公文档案、私人文件、野史笔记更能补正史之不足。毫无疑问,《旧唐书》的资料价值和可信度是极高的。褚遂良身历数朝,一生轨迹在中唐以前,属于唐当时史官所载范畴内。又,《旧唐书》是相当追求对资料之收集,褚遂良列传载文之时当在中唐,《旧唐书》“显庆三年卒”应该是可信的。笔者又翻朱关田褚遂良文论,皆同此说。
张怀 生在开元年间,虽官至翰林院供奉,而对褚遂良的了解大都不外乎传闻和史料。其《书断》记录褚遂良内容如下:
“褚遂良,河南阳翟人。父亮,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卿,遂良官至尚书仆射、河南公。博学通时,有王佐才,忠谠之臣也。善书,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显庆四年卒,年六十四。”
与前文笔者所录《旧唐书》相比,内容大致相同不能排除抄鉴可能。后人评述褚遂良口径大都出奇一致,基本上都能找到抄袭《旧唐书》的痕迹。如《述书赋并注》、《续书断》、《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等,不可枚举。张怀 《书断》惟褚遂良卒年,与《旧唐书》不符,或有传抄之误,或为传闻所困,不可知之。读张怀 所著诸文:《书议》、《书估》、《书断》、《文字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玉堂禁经》、《评书药石论》,主要以分解用笔点画,评述书风格调为主,而决非评述其人以历史家自居。
“欧阳询得虞世南,褚遂良亲师欧阳,或虞、褚同师史陵。陵,隋人也。”(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
“褚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李嗣直《书后品》)
“遂良隶行入妙,亦常师授史陵,然史陵有古直,伤于疏瘦也。”(张怀 《书断》)
以上三则论述,言褚遂良学书出处。《衍极并注》言之不确,其作者本身即不敢以肯定态度下笔。从“或云”师史陵的语气中可见,师欧阳之论点也是“或云”之断。细读之,实不可信。如欧阳得虞世南,褚遂良亲师欧阳,又怎会虞褚同师史陵呢!“或云”二字,底气不足之态可见一斑。
《书后品》言褚遂良师于史陵,此确语。但“首师虞,后又学史”恐不可信。后人书论言及褚遂良书学渊源多同此论,实是以讹传讹。卢携《临池诀》等皆载:“史陵,隋人也。”既断言隋人,其主要经历自不在唐,况初唐书家中无史陵之记录。又虞亦师书史陵,史陵当年长于虞。褚遂良入唐之前先师于史或为可解。师虞之时当在其父褚亮入秦府之后,期间褚亮、虞世南、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为十八学士,相交必深,遂良由从史陵学转至从学世南,可能极大。又,虞世南在贞观四年任秘书少监,七年任秘书监时,遂良以秘书省秘书郎在虞手下,分判课写工程。贞观元年太宗曾召集京官文武五品以上职事官的子弟:“有**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宏文)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其年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王溥《唐会要》卷**)与此同时褚遂良还担任宏文馆馆主,检校馆务,顺理成章地辅助虞世南。综上而言,如褚遂良此时求学于虞世南是最成可能的。
至于张怀 《书断》中“史陵有古直,伤于疏瘦也”一语,从论褚遂良书法中突然出现,恐怕是以批评作为褚遂良老师的史陵而间接地对褚遂良提出的委婉批评。“书如其人”一直都是书法评判的一个准则,刘熙载言之最确:“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艺概》)作者的品德操行总是与书法相互评鉴。褚遂良为唐一代股肱之臣,德艺双馨,深受太宗器重,褚遂良之父褚亮年老退休,太宗出征前特令褚遂良转达他的怀念之情:“昔年师旅,卿场入幕,今兹避伐,君已悬车,倏忽之间,移三十载。眷言畴昔,我劳如何!”(《旧唐书·褚亮传》)太宗在特使其子表示对旧臣的关怀之外,同时也有将重用褚遂良,使其父放心之意。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病重,召褚遂良等臣进卧室,说:“卿等忠烈,简在联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又告太子道:“(长孙)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旧唐书·褚遂良传》)与国舅长孙氏同为顾命大臣,辅助新君,何等器重!太宗的重用还有褚遂良善谏耿直的原因。褚遂良被认为是魏徵之后又一个著名的谏臣,他“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十上,多见采纳。”(同前)然高宗即位不久,欲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后。褚遂良以顾命大臣之身份恳切上谏:“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佳儿佳妇,今以付卿。’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又“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周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设身处地以高宗名誉着想,言辞诚切。后武氏得立,褚遂良即遭左迁,初任潭州都督,后改桂州都督。不久又贬为爱州刺使死于任上。其子彦甫、彦冲亦遭诬蒙罪。褚遂良英明气节却得流千古。《旧唐书》的作者在为其写传时,不无敬佩的评论:“魏徵、王圭之后,骨鲠风采,落落负王佐器者殆难其人,名臣事业,河南有焉。……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况于君臣之间,受托孤之寄,而以利害祸福,志平生之言哉!”博得了后人由衷的仰慕。这正是褚遂良书法多为后人赞扬而绝少批评之故。张怀 身处唐代开元时期,此时褚遂良恢复爵位已过十年,英明早定,后世敬仰。如果在《书断》中直接批评褚遂良书法,恐为忤同仁。加之张怀 尝自言可比虞、褚,其中对褚遂良甚至尚有敬重之意。那么,借对史陵的客观评价来间接指出褚遂良书法不足,则是一个最好的途径。至于史陵的作品是如何面目,世人难以得知。只知是“隋人”而已,未有片纸作品传世,即使在继隋之后的唐代也很少有对他作品的记录。这更能说明张的评价是影射褚遂良而非实指史陵而发。
四
历来书论,偶有文长无物,似理实非者。此病于明清稍重。明清士人论书,多以文采取胜,细审读之,未必确然。笔者偶见清人包世臣论褚遂良书法:“河南始于履险之处裹锋取致。”(《艺舟双楫》)包世臣此处用“裹锋”一词或意为“藏锋”,而“藏锋”与“裹锋”实全然不同。裹锋用笔,笔尖闷于笔锋之中,不能折锋铺豪,更无谈笔尖万毫齐力的攻效。而藏锋则是仅就起笔或收笔处将笔尖的痕迹用回锋等方法掩盖,使起笔处或收笔处不致锋芒太露。观褚遂良《阴符经》手迹,裹锋一说实属可笑之谈。
褚遂良用笔从魏晋而来,气息高古清雅。《旧唐书》说他“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书断》也说他“少则服赝虞监,长则祖述右军”。学虞世南书,系为时风影响,祖述右军则为求本述源。《旧唐书》称他鉴定“二王”法帖“一无舛误”,这正是褚遂良深汲右军后的结果。
“褚河南谓‘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又云:‘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周星莲《临池管见》)此论与虞世南“如抽刀断水”,颜真卿“古钗股,屋漏痕”,用笔之法一脉相承,善使笔锋,熨贴不陂。蔡希综《书法论》中言之最透,“河南用笔,如印印泥,其思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间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使取书之,山佥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者。此盖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笔者以为,所谓用笔应是能控笔、调锋、取势,三位一体,控笔、调锋重在制造点画质量,如“印印泥”等,取势则在制造书法之“山佥劲明丽,天然媚好”。世间俗书之不可医,多败于取势不当。
书法学习与创作,用笔自是首位。然纸墨精良乃至天气清爽、心情安逸亦重要。“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欧阳修《试笔》)览古今书家,褚遂良于纸墨之追求,似最为高。“褚遂良非精笔健墨,未尝辄书,不择纸笔而妍捷者,余与虞世南耳。”(《新唐书·裴行俭传》)朱长文《读书断》亦引此说。裴氏此论无非认为褚书之优雅逸美多来于笔墨精良,而非纯以功夫取胜。故不知褚遂良书风“字里金生,行间玉润”,瘦润华逸,刚柔相济。非“精笔佳墨”不能心手双畅,手笔相调,又何谈用笔流动,腕力显然。此亦可为学褚书者鉴。
褚遂良对于笔墨取舍或因习右军书法后体会如此。右军法书非笔精墨良难以拟似。褚遂良“祖述右军”或深体之。至于字体结构,后人学王,易存僵板之气,褚遂良能变张王之今古是为可敬。米芾赞曰“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海岳名言》)至于“信本伤于劲利,伯施过于纯熟,登善少开阖之势”(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实为无中有生,盖未细读褚书,妄加批评,有凑数之嫌。
(编辑:佚名)
上一篇:薛元明感觉褚遂良 下一篇:优美的褚遂良书法艺术风格